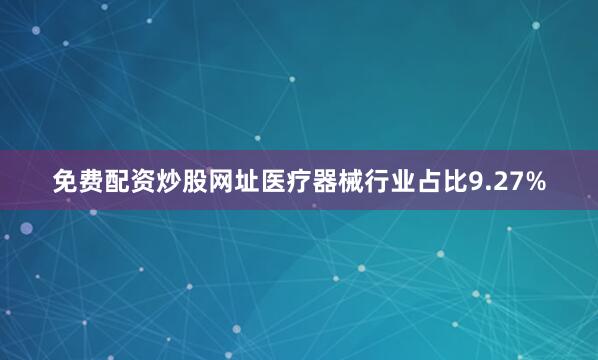瑞典外交人员的文革回忆
文革后期外交生涯
口述|罗多弼
文冯亦斐
在我成长的瑞典北部的宁静小城,家人对我求学的渴望总是给予全力支持,不论我选择学习何种知识。我对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自十一二岁起便开始学习英语,随后又掌握了俄语。1960年代初,十四岁的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访谈,他分享了许多故事,包括自己20世纪初前往中国,长途跋涉乘坐船只,抵达中国后深入内地至山西太原考察方言的经历……这是我首次了解到中国,而高本汉立刻成为了我的偶像。1964年,我有幸代表瑞典赴美参加学生交流项目,在纽约度过了三个月。期间,我有幸受到罗伯特·肯尼迪的接见,并与他进行了交谈。我好奇地问他:“为何美国不与红色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肯尼迪显得有些惊讶,经过思考后回答,美国只承认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并仅与联合国承认的国家建立外交。尽管他的解释未能完全满足我,但我心中对中国的好奇与兴趣日益增长。实际上,在高中毕业前,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学习中文。
那时,我加入了瑞典的自由主义党。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1969年,我选择退党,因为我认为自己比自由主义党更为“左倾”,对他们产生了不满,尽管如此,我也未曾加入共产党或任何其他政治组织。社会民主党1968年,我踏上了学习中文的旅程。听闻有一位名叫马悦然的年轻教授,他刚刚从澳大利亚完成学业归来,回到了瑞典。马教授不仅教授中文,而且他对文学的热情似乎比高本汉教授更为深厚。因此,我决定追随马悦然教授的脚步。
那时,欧洲各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也开始研读毛泽东的著作。在中文课堂上,马悦然教授即将为我们讲授……《左传》众多学子纷纷提议,提议我们不妨阅读《红旗》杂志。尽管他起初显得有些不悦,最终还是点头应允。于是,他为我们讲授了一整年的《红旗》。在那个时期,我实在未曾料想,未来竟会有一个职业使我日复一日地阅读《红旗》。
1973年夏天,我听说瑞典驻华大使馆要招一个年轻的汉学家来做文化专员。我就和外交部联系,说自己感兴趣。当时瑞典驻华大使正好休假回瑞典,就面试了我和其他两三个人。面试内容没什么特别的,主要是了解我是怎样的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问我结婚没,我说没有,但是有女朋友。
大使说,你要做这个工作,最好结婚。那个年代的瑞典和现在不一样,同居对外交官的形象不好。于是我在来中国前先和女朋友去登记结了婚。我得到这份工作很高兴。因为自从1949年之后,能去中国的瑞典人非常少,1950年代在中国好像只有一个瑞典留学生。1960年代能来中国学习的也少之又少。瑞典的年轻汉学家如我辈者有幸得到这样一个和中国亲密接触的机会,要归功于高本汉,是他说服了瑞典外交部设立这样一个职位。我在1970年曾经到香港短期学习过,也借机来过北京。3年后的北京,还是有一点变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整体还没有结束,但随着1969年的高潮过去。
1973年的北京已经平静了,至少表面上如此。那时的北京很安静,像个很大的大村子。随着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外国人也开始多起来。那时的我年轻且用功。外交人员服务局给我提供了一个中文老师。每天早上8点,她就到我家里来上课。上完45分钟课之后,我再去上班。当时我的中文不如现在好,一开始我们读浩然的《金光大道》,然后就读 《红楼梦》尽管老师竭力向我阐述书中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书中人物众多,要理清他们之间的联系实属不易。记得有几次,老师在课前会提到:“今天我们跳过某某页某某段不读,因为那里含有色情内容。”那时的老师已年过四十,若以今日的眼光审视《红楼梦》,那些段落又怎能被定义为色情呢?偶尔我会与她探讨一些文化话题,但一涉及政治,她便不愿多谈,即使偶尔谈论,也不过是些《人民日报》式的官方言论.
她教导我三年,我非常尊敬她,然而对她丈夫和孩子的职业一无所知,如今回想起来,这实在令人费解。除了这位老师,我们家还有一位技艺高超的厨师,也是外服局分配的。他为人热情,与我们相处融洽。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消失了。我前往外服局询问原因,他们却只夸赞我的中文水平,询问我关于瑞典主食和兄弟姐妹的问题,却不愿透露厨师的情况。直到毛泽东逝世,我们才得知他因政治原因被捕。我不知他为何被捕,或许是他的某些言论触犯了禁忌。当时,台湾出版了一套《中文大辞典》,他问我这是哪里编写的,我回答是台湾。他说:“难怪,我们这里不会出这样的辞典。”那时正值“批林批孔”,他感到奇怪,为何连孔子也要被批判。我想,他所说的这些话已经足够成为被捕的理由。我在使馆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中瑞文化交流活动,如举办中国出土文物展览、陕西户县农民画展等。
此外,我还负责送行即将离开中国的中国代表团,与他们共进晚餐,交流心得。有一次,代表团成员问我:“瑞典有没有咸菜?”我回答:“有,但和中国的不太一样。”他们担心到了瑞典要吃西餐,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吃,心里有些不安。我的第二个任务是阅读报刊,每天阅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使馆订阅的报刊,并针对《红旗》杂志的文章撰写分析报告。那时我年轻,观点不多。如今看来,媒体所反映的“文革”与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我对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大多存在误解。当时媒体强调缩小“三大差别”,我觉得很好,并发表了许多赞美之词。但现在,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那时,我从媒体上了解中国形势,并向大使和其他瑞典同事解释。其中有些话题让他们感到奇怪,比如“批林批孔”时,“周公”为何代表“周恩来”?
那时,使馆里除了我,没人能理解这些。那三年,我在工作之余与太太散步、看书、品尝美食——外国餐馆的美食丰富,书店里也有不少古籍可供购买,散步时也无人打扰。至于娱乐,我看过8个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等,反复观看。其实,我认为样板戏本身并无不妥,问题是当时没有其他娱乐方式,戏剧领域只有样板戏独领风骚。相声、快板等因政治要求过于严谨,缺乏幽默感。总的来说,那段日子我们过得还算愉快。然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无法与普通人交流有趣的话题。我的老师马悦然在1950年代也担任过这个职位。那时的北京比我在的那几年要自由,他与文人、学者交流的机会比我多,收获颇丰。我的收获虽然也不少,但大多是来自阅读和报刊。遗憾的是,我并不认识多少文化人。
那时我的交际圈很小。和普通人没法太多交流,和中方的高级领导人接触的机会也并不多。1973年9月,我刚来北京任职后不久,瑞典国王去世,瑞典大使馆邀请中方来使馆悼念。邓小平那时刚平反不久,他率人前来使馆,他非常矮,眼神很敏锐。表达能力特别强,也很务实,比如,他说如果要开会,就一定要作出决定。关于样板戏,他曾经说了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话,大意是说样板戏好是好,就是他个人不感兴趣。邓小平在政治上特别聪明,1973年他的复出已经是一个奇迹,更没有想到他很快就成为中国的领导人。
当时的外长乔冠华也值得一提。有一年,瑞典大使离任前,他邀请我们使馆同仁去他府上做客。我们一个晚上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那一晚他和我们干了很多杯酒。他很有风度,讲话在当时的政府官员里算是很大胆的了,也爱开玩笑。那些日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76年的一天,周恩来遗体要火化,我和太太就在医院外面,四处都站满了人。当灵车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大声叫起来:“别烧!别烧!”很多人都在哭,毛泽东去世时,我刚离任,打算取道广州去香港。是广州旅馆里的服务生告诉我这个消息的。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的态度与周恩来去世时老百姓的态度不一样。
服务生没有表示什么感情,虽然看起来有点紧张,但没有显得特别悲痛。我感觉毛的去世可能并没有使人们感到像周去世那么悲痛,这可能是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周恩来要安定,反对乱;而毛泽东主张斗争和革命。有一次,马悦然陪瑞典驻华大使去递交国书。大使和马悦然提前准备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言稿,说中国的文化多么好。毛泽东听了以后,说:你们说得太过分,中国文化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有三个东西值得保留:一个是《红楼梦》,一个是中医,第三个你不好猜:麻将。
1950年五月,瑞典荣膺首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誉。这一历史性时刻,无疑与其当时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在那个时代,美国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方,众多欧洲国家亦步其后尘,唯美国马首是瞻。然而,瑞典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中立国瑞典当时的外交政策,不受美国左右,其主导者,瑞典外长Sten Undén博士,乃国际法领域的专家,略带反美色彩。瑞典的外交走向,主要取决于他的决策。在他看来,与某个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对该政府产生好感。简言之,依他的观点,只要一个政府实际控制了某片领土,便应承认其国家的合法性。冷战时期,中立国得以拥有更多独立行动的空间,瑞典遂淡化其在中国的“西方国家”形象,转而强化其作为“桥梁”或“媒介”的新角色。美国并未因中瑞建交而与瑞典交恶,反而两国关系维持得相当融洽。
尽管中瑞间的交流并非频繁,但双方关系却颇为融洽。20世纪下半叶,瑞典人对中国及其人民的认知发生了何种变化,实为一大引人深思的话题。19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与中国的“文革”,吸引了瑞典人对东方及第三世界的关注,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并促使他们进行思想上的转变。自那时起,瑞典人对中国的看法亦随之改变,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如唐诗宋词,或宋代的瓷器等,而是转向当代中国社会与生活。在这一领域,中国的“文革”引发了众多瑞典人的兴趣。当时,许多像我这一代的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都曾以为“文革”解决了我们西方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官僚主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等。然而,后来我们才意识到,这不过是对“文革”的误读,我们没有意识到其所带来的灾难,中国人为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瑞典人认为中国十分出色。中国正走在一条能让大多数人生活迅速改善的道路上。
我们通过“文革”的宣传,认为其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当时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极为有限。随着中国逐渐取得巨大进步并日益开放,我们开始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不足之处,因此,今天的中国形象相较于1970年代更为负面。然而,事实恰好相反,如今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相较于1970年代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在瑞典历史上,中国形象,尤其是作为一个赶超的榜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8世纪,学者卡尔·舍费尔在传递中国影响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的老师。古斯塔夫三世在位期间,国内政治问题严重,国王与贵族间权力斗争激烈。国王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扩大自己的权力,限制贵族的权力。于是,他发动了政变,政变需要意识形态和舆论工具的支持,而中国恰好充当了这一角色。国王的目标是让瑞典成为一个像中国一样的国家,以此强化自己的权力。在政变期间,费舍尔先生是他的亲密顾问,为国王进行了多场演讲,宣传鼓动,将中国描绘得近乎完美。
当时,瑞典国王并不认为自己美化了中国,他认为所获得的中国信息都是真实可信的,中国正是一个理想的国家。由于他对中国的了解有限,因此未能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方面。而如今,众多中国官员和学者纷纷前往瑞典参观,将瑞典视为一个理想化的国家,试图学习瑞典的模式。无论如何,在中国,有人主张民主与平等,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积极的转变。现在,中国人对国外的情况充满好奇,渴望了解世界。有时,我发现中国人的进步很大,而瑞典人却相对滞后。例如,许多瑞典大学生不愿出国,因为他们认为在瑞典生活已经很好了。实际上,瑞典的社会问题也不少,如高失业率,尤其是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这实在令人担忧。然而,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瑞典的问题相对较少。
瑞典社会贫富差距不大,且较为和谐——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现在的中国与1970年代大相径庭,但依然存在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环境污染、贪污腐败等。中国只有真正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成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罗在北京度过了三年)

靠谱的实盘配资平台,实盘配资平台,专业炒股配资门户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